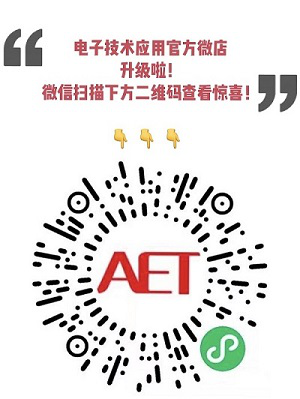基礎設施顧名思義是社會運行的底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十多年來,隨著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和4G/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互聯網服務興起并滲透到經濟社會民生的各個領域,促進通信基礎設施向著寬帶化、云化和軟件定義迅速演進,而且新一代信息技術作為通用技術正加速融合到傳統行業基礎設施中,信息基礎設施也已成為傳統行業基礎設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通常先進技術都有雙刃劍的特性,信息技術尤其如此,在加快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和高效決勝于千里之外的同時,其漏洞與薄弱環節也容易被惡意利用。基礎設施對信息技術的依賴性越深,其受影響就越大,特別是對重要行業和領域,基礎設施的安全問題可能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公共利益等,因此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保護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
安全形勢錯綜復雜
關鍵基礎設施安全受各國重視
隨著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加劇,網絡安全事件與地緣政治熱點有明顯的結合趨勢。特別是個別國家拉攏盟友以網絡安全為借口打壓中國信息技術企業,斷供關鍵元器件并限制我國產品出口,既為他們的產品搶占中國市場獲得經濟利益,又削弱了我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自主可控的能力。網絡安全攻擊也被利用來針對我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已經出現有組織的網絡安全攻擊矛頭直指中國的趨勢。現在個別國家的軍隊從網絡安全攻擊的幕后走向了前臺,美國2010年就率先成立了網絡司令部,使網絡作戰與空中、太空作戰充分融合,2017年8月升級為一級作戰司令部,正式將網絡攻擊作為戰爭手段。
世界各國也紛紛出臺法律法規,加強關鍵基礎設施安全保護。美國2001年起先后頒布了《2001年關鍵基礎設施保護法》《改進關鍵基礎設施網絡安全行政令》和《增強聯邦政府網絡與關鍵基礎設施網絡安全行政令》等相關法律文件。明確規范了保護重點、多層次保護組織架構、風險評估方法和衡量評價方案及指標體系。歐盟從2008年起出臺了《2008年歐盟關鍵基礎設施認定和安全評估指令》和《2016年網絡與信息安全指令》等關鍵基礎設施保護法律文件。從制定歐洲廣泛適用的標準和方法、建立歐洲信息共享和預警機制、制定應急預案并進行應急響應和恢復演習等方面確保互聯網的穩定性和應急能力為歐盟優先發展事項。日本在2005年制訂并于2009年和2015年修訂《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信息安全措施行動計劃》,規范了正常與危機時的信息共享機制、跨部門的演習與培訓、國家與運營者的二級風險管理、標準認證與國際合作、相關方的利益與行動等。此外,不少國家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保護也出臺了相應的法律。例如俄羅斯2017年頒布了《聯邦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法》,澳大利亞2018年頒布了《關鍵基礎設施安全法》。
我國安全保護實踐積極開展
成果顯現但形勢仍然嚴峻
早在2014年2月,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要抓緊制定立法規劃,完善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等法律法規,依法治理網絡空間,維護公民合法權益。”在2016年4月召開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加快構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障體系。金融、能源、電力、通信、交通等領域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運行的神經中樞,是網絡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可能遭到重點攻擊的目標。“物理隔離”防線可被跨網入侵,電力調配指令可被惡意篡改,金融交易信息可被竊取,這些都是重大風險隱患。不出問題則已,一出就可能導致交通中斷、金融紊亂、電力癱瘓等問題,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和殺傷力。我們必須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切實做好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防護。
2017年11月,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其中有專門一節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行安全”,要求在等級保護制度基礎上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實施重點保護。同年發布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征求意見稿,與國家《密碼法》、《數據安全法》等一起作為網絡安全法重要配套法規,歷經四年多的實踐,《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將于2021年9月1日起實施。
這幾年的實踐表明,國家網絡安全法及其配套的政策法規對促進我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保護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據工信部網絡安全威脅和漏洞信息共享平臺監測數據,2021年上半年我國DDoS攻擊次數同比減少51.9%,僵尸木馬受控事件同比減少58.8%;境內惡意程序傳播、惡意程序控制端IP地址和域名等惡意網絡資源同比下降67.4%,被篡改網站數量同比減少86.5%。
但同時要清醒認識到,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網絡安全形勢仍然嚴峻,網絡安全漏洞和相關攻擊行為仍然在持續增長,2021年上半年,工信部網絡安全威脅和漏洞信息共享平臺新增收錄的網絡產品漏洞已達到2020年全年的58.5%,利用漏洞對境內主機進行掃描探測、植入木馬等遠程攻擊行為的惡意IP超120萬個,55.7%來自境外。特別是針對電子設備、專用設備、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等重要工業互聯網領域的網絡攻擊仍在持續增長,2021年上半年,國家工業互聯網安全態勢感知與風險預警平臺監測到針對我國工業領域的網絡攻擊同比增幅超2倍,遭受網絡攻擊的工業企業數量同比增長57.2%。勒索病毒攻擊仍然異常活躍,據Cybersecurity Ventures的預測,到2021年全球勒索軟件破壞成本將達到200億美元,是2015年的57倍。利用產品軟件官網或者軟件包存儲庫等進行傳播的供應鏈攻擊已成為2020年最具影響力的高級威脅之一。據 VenusEye 威脅情報中心數據,過去一年多,在全球受僵尸網絡控制的各類物聯網設備中我國占比最高。從全球看,2020年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事件越來越隱蔽而且危害越來越大。
法治保障意義重大
將為網絡強國建設奠基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面臨著錯綜復雜的嚴峻形勢,為了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第二個百年發展目標,國務院正式發布《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意義十分重大:
一是該條例定義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給出了認定規則的主要因素,明確了認定的責任主體及程序。二是該條例突出了國家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總體部署與統籌協調,界定了國務院相關部委及地方政府的職責,堅持綜合協調、分工負責、安全保護和監督管理。三是該條例明確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主體責任,包括制度建立、組織落實、經費保障、教育培訓、監測評估、應急演練和定期報告及事件報告,以及違法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等。四是該條例對建立網絡安全生態鏈給出明確的要求,即安全保護措施要與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三同步(規劃、建設、使用);運營者需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設計、建設、運行、維護等服務實施安全管理;運營者應優先采購安全可信網絡產品和服務,并通過與供貨商簽訂安全保密協議和監督以明確提供者的技術支持和安全保密義務與責任;國家優先保障能源和電信等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運行,能源和電信行業應為其他行業和領域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運行提供重點保障;國家支持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并組織技術攻關等。五是細化了操作的紀律要求,例如安全檢查工作不得收取費用,不得要求被檢查單位購買指定品牌或者指定生產、銷售單位的產品和服務。在安全保護工作中獲取的信息,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未經國家有關部門和運營者授權,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實施漏洞探測、滲透性測試等可能影響或者危害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的活動。
總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將我國網絡安全工作的實踐經驗總結并上升為法規制度,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工作提供法治保障,同時給出了可操作的執行要求,將有力支撐我國網絡安全技術和產業的創新發展,為網絡強國建設奠定堅實基礎。